-
 Simple and Best
Simple and Best
-
 Simple and Best
Simple and Best

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安邦的方法是建立在信息分析方法论基础上的,信息分析方法论才是我们的根基,这是我们自己的研究范式。
研究员的工作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智库的工作内容都是什么?2021年9月,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先生在内部的深度讲话《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中为大家阐释过。
职场心里话接下来,将会用五期的内容,为大家深度解读,安邦智库究竟聚集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究竟是你厉害还是大学教授们厉害?
第四个问题也是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问的,究竟是你厉害还是大学教授们厉害?
让我回答问题,心情有点尴尬,按说这是由别人评论的问题,不是应该由我来自我评论的。既然今天讲到这里,要做一番我自己的白描,所以不妨就谈一谈我自己的想法,我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我是怎么比较的。虽然跟大学教授的比较是有点尴尬,但是在这里就不回避了,勉强比较一下。
按说大学教授厉害的地方应该是数量分析、数学分析,像分析汇率的弗莱明模型、古典增长模型等等,像凯恩斯政策一类的大家都看过、都知道。其实我对数学是很崇拜的,我甚至认为经济学家就是用数学模型的人,就是能够将理论关系翻译成数学语言的人,否则一定就是新闻记者冒充的假经济学家。那么关键是,在这种数学模型崇拜的背后必须有数据,关键是有数据,如果没有数据,那不就是一切都是瞎扯了。
对数据我们要有所了解,我相信对数据的使用、对数据的这些知识大学里面都教过,无论你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还是在中国的大学里面,这是最起码的、最基础的知识。应该懂得数据是分成两类的,一类是主观数据,一类是客观数据。
客观数据就是那种大自然的数据,太阳距离地球有多远等等,这就是客观数据,还有山川河流的改变,所有的这一切来自于大自然,包括分子、原子啦,物理学家就是干这些的,这些都是客观的东西,都可以形成客观的数据。
主观数据,其与客观数据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主观数据跟人有关系,跟人有关系的数据才是主观数据,这种跟人有关系的不得了,因为凡是跟人有关系的数据,人都有参与度、都有一定的介入性,那么人就可以去修改,甚至在过程当中制造数据,这就是不可控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现在世界没人敢拍胸脯说主观数据一定像客观数据那样可靠,没人敢做保证。
不会有一个宇航员会坐经济学家设计的火箭到太空去旅行的,这就是原因,他们一定是会做物理学家设计的火箭升空的。马斯克绝对不会请经济学家来设计火箭的,原因就在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还有跟社会研究相关的所有的领域里面,如果你应用的是主观数据,那么主观数据仅供参考,并非绝对的,它不是绝对真实的、不是绝对准确的。这种绝对的不真实、绝对的不准确,才是主观数据真实的一面。

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实际上也包括世界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数据实际上这种大规模的应用,数据驱动这个词儿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但实际上它导致了一种“数字化的模糊”。数字化的模糊是一种事实、是一种现实,它是真实存在的。数据越多,创造的这种模糊就越多。本来清楚的事儿,经过数字的这一番修饰,你会感觉它不对了,就不一样了。比如说现在的数据表明你的生活水平有了惊人的提高,你就会想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但从数据方面来看又确实如此。这就是数据的模糊。
跟大学教授们相比,大学教授们是非常注重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们是非常注重数学模型的,还有就是西方的大学、美国这些大学里面毕业的人,他们在工作当中都善于大量的使用数据。比较起来,西方国家的数据因为法律、法规、环境的不同,相对的存在一点儿真实,但是这种真实并没有改变我刚才说的“绝对的不真实”和“绝对的不客观”。
跟政治、社会相关的,凡是跟人相关的都会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所以我才会说它是一种数字化的模糊。这种数字化的模糊是我们现在的世界必须要面对的挑战。数字化模糊问题只能在研究过程当中,做研究的人不断地加以修正,一边做研究一边加以修正,保持这样的态度去做研究才可以形成一种真实的、可信度比较高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保持一种绝对化的这种态度,面对这种数字化模糊,就认为是“我是基于数据的,我是基于模型的,我是在数据模型基础上得出结果的,那就是一定是正确的···”这只会闹笑话,只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独立智库,一旦失去了信用,就什么都不剩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不敢完全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建立在数学模型的基础之上来做研究。我觉得,这是我不如大学教授们厉害的地方。
对于安邦来说,我们的方法跟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安邦的方法是建立在信息分析方法论基础上的,信息分析方法论才是我们的根基,这是我们自己的研究范式,这一点跟大学教授们研究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比较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清楚这一点。如果说不清楚这一点,别人就会跟你一直做比较。
实际上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拿汽车跟拖拉机进行比较。拖拉机耕田一行一行、直来直去,田地耕出来都是一道一道的,我们看上去都非常的规整,横平竖直,但是安邦做的东西要适应四面八方的改变,适应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变量因素,必须把它综合在一起加以考量,只有能够适应这种现实的方法才是我们可以运用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就是信息分析方法论,就是信息分析的范式。这种方法论和范式跟世界各国情报机构的方法和范式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培训当中也会提到和讲到,这是因为他确实是有相通之处的。但这种方法跟大学、跟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那种研究机构是大不相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在安邦工作的人一定要知道。
那么比较起来,究竟哪种更好一点?
我觉得可以开放式的讨论和评价,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这是我粘贴下来的大学教授们的讲话方式:
“不,我只是认为美国目前正在违背其价值观和自身利益,这是双输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输了,在原则上输了、在利益上输了,我不相信美国进行交易等等想法。我认为当代美国背弃它的使命、例外主义、信条等等,对美国其它地区都是不利的,它不是繁荣的源泉,恰恰相反。所以我的希望和我的信念是国家将再次与其信条和自身利益相匹配的时候会到来,可能比美国人想象的还要早。”
这是我直接粘贴下来的一段话,大学教授讲的很热闹,但是不解决问题、听不懂、无法理解。我对这种玩弄语言技巧的游戏从来就没什么兴趣,我从来不搞评论。在安邦的产品简报当中,我最反感看到的就是评论。评论在我的眼中就像一粒沙子一样,让我很难受,这是我一个非常讨厌的东西,一定要把它除之而后快,除非是必须的解释,也就是以解释为目的,毕竟有客户听不懂,所以我们要加以解释,有的人把这种解释认为是评论,这种情况是是允许的。
我做了一辈子的预测和判断,如果稍微客气点说,就是前瞻性分析。这跟大学教授们就完全不同了,大学教授们虽然也懂预测和判断,也做模型之类的,但一般是不做预测和判断的。那个风险太大了,还出不了名,最后预测错了、判断错了,是不是要更新、更正?几十年来我好像从来没有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上看过哪个大学教授认错了、判断错了。
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只有余永定,这是一位社科院的经济学家,他曾经公开自我批判过,很有勇气的说自己过去在什么事情上判断错了。至于其他很多厉害哄哄的、网红性质的那些大学教授们从来都没说过自己错过,都觉得自己跟上帝一样,后边是需要系统保证的,如果你没有那种能力,你没有这样的研究体系来支持,世人一定是要犯错的,不可能不犯错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把事情搞清楚,把思维整清楚,精细化非常重要。很多事情都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的,像我跟大学教授们的比较就是这样,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标准不一样、体系不一样、范式不一样,还偏偏要去比较。这种比较可能就是荒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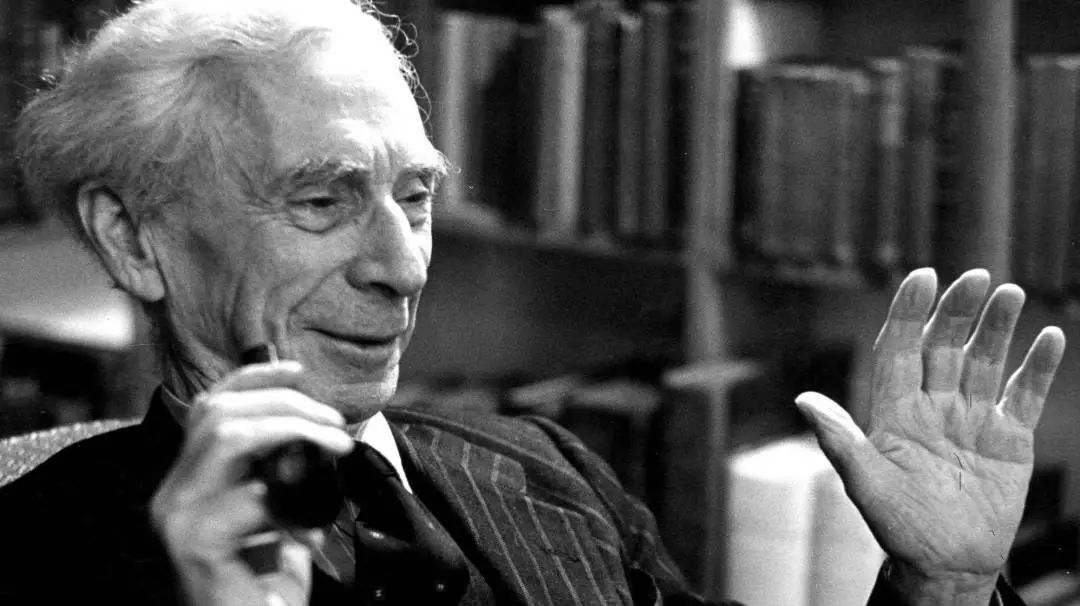
罗素认为,他通过数学能够实现一切。我觉得没问题。罗素讲这句话没问题,从他的角度来看是没问题。我是通过追踪、观察来实现的,我是通过时间序列的观察来实现的。有点像化学家做实验一样,在瓶瓶罐罐的实验室里面做一些实验,观察他的反应,然后得出结论,这一切都必须观察,紧盯着他,也就是说追踪研究才能够行。我觉得这一切的结果是可以反过来,用数学表达的,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要说直接从结果来倒推,我通过这些数学的结果、通过这些结果性的数学就知道了未来。这是不现实的,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大多数这方面的量化研究都是理论性质的、都是在课堂之上的、都是在大学里面进行,但不要因此而误会,它真的可以投入实际去做,而且我们更加可以去相信这种结果。这是一种荒谬的迷雾,它是一种数字化的模糊,我觉得这一点要跟大家讲一讲。
究竟最后还是要回答“我厉害还是大学教授们厉害”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可能会关心这个问题,也会比较这一点,他们想通过比较这一点来知道安邦的产品、安邦的简报、安邦的观点是不是真的有价值,这是可以理解的。
怎么去比较呢?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我预测完了一到两年的事情,也许还有更长时间的,我预测完了之后,七年、八年、甚至十几年的事情,才会有人跟进进行研究,它才会变成一个事情,才会被很多人、被大学教授们认为这真的是个大事儿了,因此要加以研究了。这里边是有一个巨大的时间差。我觉得一般常见的是一到两年,也就是说,一到两年之后,大学教授们才跟进,才对我的思想、观点,我过去指出的那些东西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我觉得这种差距就已经说明了所有的问题。
当然也有人说,你的研究就是瞎猫撞死耗子。想一想,我几乎所有的预测、判断、研究,虽然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就有几大本书这么厚,把这些预测、判断的结果列出来,最后形成了几大本书。也就是说,确实看到了有这么多的成果、这么多的思想观点摆在那里。但还是会有人说这就是瞎猫撞死耗子,说的人太多了,后来我干脆就自己养猫了,咱们办公室的那个猫就是专门用来撞死耗子用的,所以看见了猫,实际上就是在提醒我们大家,咱们是搞预测的,咱们就是专门去撞死耗子的。
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些东西,还有两大部分是外界一般不知道的,几乎是不会注意的也永远不会注意的,看简报的人看了跟没看一样的,就是“有的事情隔了几年它是会兑现的,有的它是永远不会兑现的”,这两部分是同时存在的。这些着眼于未来的预测与判断、思想与观点,都属于战略性政策的一个部分。战略性政策一定是要看将来的,他是大是大非、大政方针。什么是战略性政策?战略性政策就是层次,另一个则是时间。层次高、时间长,就是战略性政策的特点。
安邦就是一直做战略性政策研究的。我们做信息分析、做追踪研究,做了一辈子,做了这么长时间。这工作是干什么?就是服务于战略性政策。安邦是专门在做、真正在做大政方针的研究,准确地说,就是在做战略性政策研究和分析,这是安邦的主要工作,也是主要的领域。这部分工作都是跟长周期有关系的。
如果你看到说安邦做的东西一两年之后成为了现实,事情爆发出来了,人人都关心变成了热点,这很正常,这就是安邦做的工作。当然也有那种立即就发生的,立即就兑现了,几天以后事情就变成现实了,就变成热点了。这种事情也有,但是相对来说,安邦是做得周期更长的那些事情,价值含量更高的。这一点是我要是要告诉大家的。

比如说,今天我们人人都知道集装箱价格不断的上涨,据说已经上涨了十倍(注:该内容成文于2021年9月),严重影响了进出口,影响了经济增长,严重干扰了国际贸易。很多人对未来生意的前景忧心忡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事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在分析电商的时候就指出的问题,那个时候就已经清楚地告诉大家,物流成本会成为核心的影响因素,有支配性力量的是物流成本。因为大家都转向了电商,电商是需要物流的,它是仰赖于物流的。没人给你送东西,哪还有什么电商平台,所以物流会变成一个支配性力量。
很早以前我们就讲,可是没人听得懂,没人会仔细去想一想,也不认为这个事情是有价值的。如果认为是有价值的,大家不都一哄而上去做物流了。既然做的人很少,看到的人很少,所以大家对物流是忽视的,才会今天遭此大难,才会明白运输的成本对自己的生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类似这样差个一两年,差个七、八年验证的事情在安邦太常见了,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几十年的问题今天才显现,这对我们来说是习以为常的。对一般的人来说、对社会大众来说,他们可能觉得某件事儿是很新鲜的一件事情,甚至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总的来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跟大学教授比起来谁更厉害一点,我只知道我讲的东西要在几年以后大学教授们才开始研究、讨论和评论,这是我能给大家的我的结论。
你的名气大还是网红的名气大?
第五个问题,讲讲名气的问题。因为有人跟我这么比较过,说你的名气大还是网红的名气大?
我面临的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两难的情况。问题是越做越深,那就无人能理解了,永远成不了网红。如果要选择大众议题,如吃喝拉撒睡,这些很受欢迎,非常容易成为网红。像《舌尖上的中国》很多人都爱看,整天都是吃的东西,各种各样好吃的。讨论这些吃喝拉撒睡问题的,都很容易成为流量、成为明星,在流量上容易赢得支持,自然就会成为网红。
这里边还有一个“看得多、看得少”的问题。你看得越少,实际上就越容易成为网红;看得越多就想得就多,想多了就越来越深入了,那就很难成为网红了。听都听不懂,怎么才怎么能理解呢?
我记得本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一首好诗,要忍耐五百年不被阅读和理解。”这句话容易听懂吗?似乎容易,但实际没人真懂的,除非你能做到那个程度,五百年后人家才明白。
语言技巧好不好学?至少对我来说应该不算难学。但这里面对我来说有一个巨大的障碍,语言表现要想说的好玩儿,就必须信马由缰、突破框架,甚至没有框架,这样才会聊得兴高采烈。
这年头要是不说废话,那是很难红起来的。思想和写作研究逻辑讲究框架,没有框架,那就变成散文了。所以这样看下来,这两者实际上是矛盾的,是互相对冲的,我只能顾一边,我觉得听得懂就听,听不懂那就等待五百年。这里边的矛盾和障碍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谈到网红问题的时候,我当然理解大家的心情,如果在安邦有一大帮名气很大的人,像网红那样的人物,很有号召力,能够带来流量。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说话有人听嘛。实际上这中间是存在矛盾的,我觉得就像是世界上的一些知名人物,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是讲究适可而止,也不是说拼命的、不惜一切代价的、不计后果的去追求名声、去追求网红,像中国这么疯狂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我也注意到了,像罗素这些人物,他们都非常有语言表达的技巧。一种成功的概念、一种理论,要想传播开来,确实需要借助一定的语言技巧。这一点是应该承认的。但是这种追求不能走到疯狂的程度,不能走到那种网红的、那种狂热的程度。到了那种程度,我前面说的这种障碍就会表现出来。我们看到的很多世界上的理论家,他们的表达都非常流畅,甚至已经有自己的个人风格,也很注意这种技巧,他们也因此得到了一些类似于网红的收益。
比如说贝尔纳德·里维(伯纳德·亨利·莱维 - Bernard-Henri Lévy),他是一个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到处演讲、答疑、回答问题,实际上真正的大师、大腕儿们、权威专家学者,他们主要做的工作就是答疑的工作,就是访谈、回答一些问题,通过这种公开的、这种沟通形式来扩张影响力,传递思想、理论和概念。有的人也确实是有一些附带收获,比如说就刚才提到的莱维,他前前后后娶了四个老婆,还有一些情人,法国风格的学者都是避免不了的,毕竟浪漫的法国人嘛,他们在这方面可能是习以为常的。其实严肃的学者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罗素,就很讨女人喜欢,也是结过四次婚,七老八十了还结婚。我想这都是边际收益,都是因为自己的名声传播好所导致的一些网红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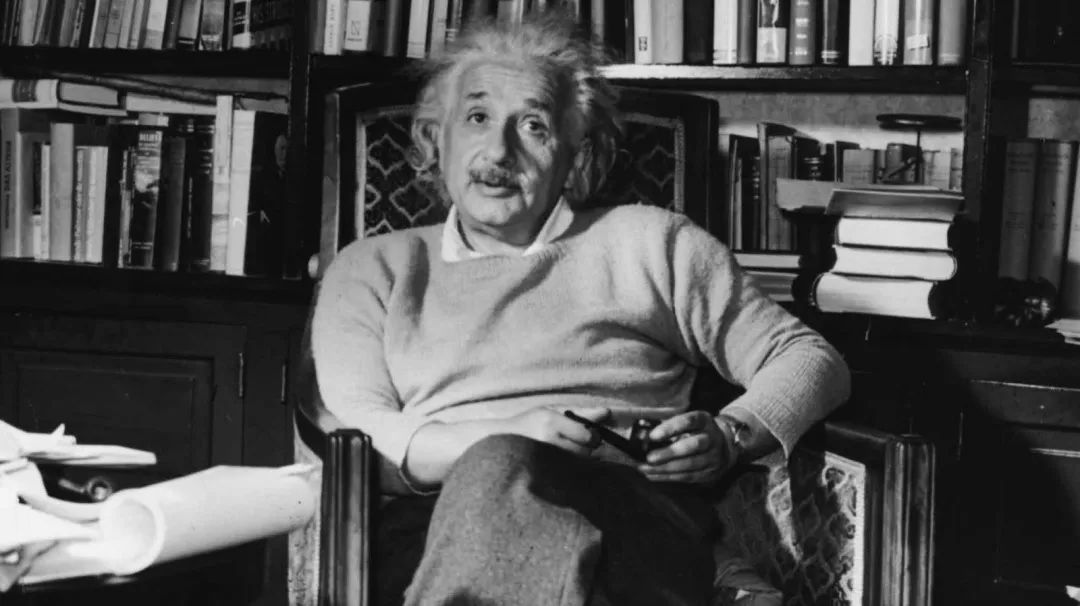
爱因斯坦在后期,主要工作也不是做研究、不是搞科研,他同样也是在做演说,转身成为了一种公共知识分子,扮演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科普的角色,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跟网红的这种疯狂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存在一定距离的。没有像中国这样疯狂,中国的网红几乎是不顾一切的,为了红,为了流量,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情都敢做,不顾一切、不顾后果,无论正确与否,流量为王,一切都是为了流量。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这可能跟社会的成熟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成熟的社会是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去这么疯狂追求流量的事情的,只有不成熟的社会,因为没有办法,选择的空间比较小,那么就只有这样去追求这些东西。这样的做法实际跟学问、学术、研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距离,他不是在做研究,他的目标根本完全不是为了做研究、做学术,他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流量,只是为了名声,要成为网红。我觉得这其中的差距是很明显的,要有所取舍。网红的名气大,那是有代价的,要付出成本的,很有可能这种成本会影响一生。我觉得做网红这条路要有理性,如果不理性可能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了。
当然我不反对大家去追求各种语言技巧,实际上我看到的很多的清谈节目,很多的视频都是属于这种语言技巧节目,我还是很鼓励大家这样做的,比如我就出了个主意,市场部门的人可以试一试直播,材料在安邦都是现成的,内容也都是现成的。要论起来,当网红条件要比外界东拼西凑、东拉西扯的要强得多了。我是希望看到能够出一些网红的,这要看你们自己的追求,不下点功夫,那肯定是不行的。实际做起来大家可能就会发现也没那么容易,要想成为网红,学到的东西一定还有很多。
至于我自己,我当然也希望有点名气,没有人不希望,但是我觉得我有底线,我有自己的标准和原则。我做的有些东西我看基本也就是这样了,很多的东西,有一些讲的事情或者观点,可能按照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也需要五百年后才明白。
像我这样的人,我真的想过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说的好结果就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所谓的好结果。因为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和工作,越做越深、越做越深刻,你向深处去探寻,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没有朋友、没有友情、没有亲情,谁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谁也不知道你在干吗,走到最后可能就是四大皆空,谁也不明白你,谁也不懂你。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挺好。人生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你还真能买几个大宅子带进棺材里面吗?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这样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