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mple and Best
Simple and Best
-
 Simple and Best
Simple and Best

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我所做的工作是做的一个独立智库,独立智库是今后世界的未来。
研究员的工作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智库的工作内容都是什么?2021年9月,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先生在内部的深度讲话《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中为大家阐释过。
职场心里话接下来,将会用五期的内容,为大家深度解读,安邦智库究竟聚集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你是干什么的?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干什么的?
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是干什么的,我家里人也问,这个问题后来变成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了,我自己也经常问我自己,你究竟在干嘛?你这一辈子究竟做什么了?
开始的时候,我想了很多的答案,有很多庄重的答案,也有很多壮丽风格的答案,都是那种气势磅礴的告诉大家我是干什么的。后来想想,这些答案都不对,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自我。
我们曾经做过几本书,这么厚的、很大本的那种书,书里写的东西都是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开列了一份清单,把我们做过的事情都一项一项的列出来,这些事情就有几大板块,非常的好,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真的,我们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想来想去呢,要想把它归纳总结起来,把这些事情用一个什么方法把它概括一下、形容一下你究竟是在干嘛呢?我暂时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思来想去,我其实也没做什么特别值得一说的事情。一句话,我也就是每天随便看看。这就是我的职业——随便看看。
其实,这个随便看看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小文章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错误、失误,跺着脚说后悔的人太多了,犯错的原因看似千变万化,像有大麻烦了、出问题了、产生矛盾了,或者破产倒闭了,但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正确的答案,真正的问题,那些跺着脚说后悔的人所没有提及的、没有讲到的真实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源自于三个字,“不知道”。如果你看的东西特别的多、看的时间特别长,什么都看,这时候你就会从不知道转变成为知道。看与没看,知道与不知道的差别可太大了。这个跨度就是成功与失败之间的跨度。有的人一张嘴就知道你看没看,有的人一张嘴就知道你看了多少,一张嘴就知道你是真看还是假看。就是看一看,但是这看一看是有名堂在里面的,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包括了很多的情境,都是在看一看里面。有的人看一看什么也没记住,就这么过去了。对我来说就不一样了,我必须要有办法能够记住那种车窗中划过的每一道风景,这当然需要技巧,这就有了专业和职业,也就有了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不是随便看一看,有的人说我也随便看了,你看什么了?为什么去看?这里面是大有讲究的,我们家保姆也天天看手机,看的时间比我长得多,真是抱着手机睡觉的,但她不会来安邦工作的,因为她看的东西没用。知道该看什么,那是一个标准,那才是真正的水平。这样看得多了就知道,那不是一般的风景了,那是人生。于是研究人员的生活也就有了。
你是不是真的在做研究?看的不是你的学历、抬头,不是名片上写的XX教授、XX官称,不是这些东西,甚至不是你获了XX奖,真正看的是什么,就看的是你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那你一定是真的就在做这件事。
中国人是比较讲究修行的,很多人都听说过修行这个词儿。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知道在终南山上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修行。什么叫修行?修行就是坐在那里沉思、冥想,这就是修行。我觉得这种修行是一种生活,是一种修炼。凡事如果到了修行和修炼的程度,就一定能成。是真的、假的,只要一看有了,那么就真的有了。所以事情到了一定程度也就是成长了,尤其是对一个研究人员来说,我就是这样过来的。从过去到现在,就是随便看看,每天随便看看,这样看来看去,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就这样过来了。于是每天随便看看就变成了我的修行方式,就变成了我的修炼方式,我就是在这其中修行和修炼,来实现我的追求。
所谓研究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所以我真的没干什么,我到世界上来就是随便看看。
你的工作有意思吗?
第三个问题,我想回答一个问题,问题是你的工作有意思吗?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际可以转变成为另外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傻?你的工作要是没意思,那你干了一辈子那岂不是很傻嘛。所以问题也可以转化成你是不是傻?这是个大事儿,是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同样,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很多,从含糊不清到别人说的都有道理,到慢慢的形成自己的见解,再到自己坚信不移的相信自己的见解。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走到了这一步。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思的,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所做的工作是做的一个独立智库,独立智库是今后世界的未来。
独立智库是未来,这是我现在坚信的,过去我可不是这样想的,过去跟大家一样也有很多的追求,所以方向是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现在我就相信独立智库是未来。为什么这么说?这里边也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今天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
大家都知道世界是很大的,做这种研究工作的机构就有非常多,像政府部门就有在做研究的,大学里面也有很多人在研究,还有社会科学院,还有很多的智库也都说在搞研究,写个报告也都是很漂亮的报告、煞有介事的报告。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新闻媒体难道说不在做研究吗?如果你问他,那我想他们都会告诉你,“我们也在做研究啊”。世界上做研究的人可能有很多,但是研究和研究不一样,我们都在谈“研究”这两个字的时候,在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要知道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今后的世界是个混沌的世界,太混乱了,我们现在自己就看得乱得不得了。过去几年的政策可能今年就不一样,可能未来就更不一样。过去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变化也是非常之大。几年前我们都在谈全球化,乐观的不得了,有无数的大腕儿们、权威人士,看上去很有资格谈全球化的,这些人都对全球化充满了乐观,他们反复地在讲,甚至因此还挣了不少的钱。今天我们再一看全球化,很多人都知道这已经不一样了,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了。
房地产也是这样。过去房地产是经济的支柱产业,不止我是这样看的,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看的,非常的乐观,对产业的远景。房地产大亨自己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更是乐观到癫狂的地步,认为自己在中国人的群体里面,他是处于金字塔尖上的人物。他们自豪的不得了,当然也自傲得不得了。这种盲目的傲慢支配了他们的行为,所以他们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房地产业也渐渐接近于颠覆的边缘,我们就可以看到房地产濒临破产,或者已经破产,就已经有很多很多。世界的变化很大、改变很大,这种变化和改变已经是触目可及,随处可见。
今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我们不能不关心、不能不去思考。不知道这种情景,那么未来就无从谈起。我的看法是,在这种急剧改变的形式面前,今后机构可能也不行,大学也不行,权威、大腕儿更是不行。机构部门主要是在执行层面做事,它不一定就能够扭转这些形势,有能力扭转这种大局。放眼历史,从历史看现在,决定历史走向的只是少数人,决定形势改变、出现转折的都是少数人。并不是说大家所看到的那种庞大的机构,无数人在里边工作的、打着官腔的这批人,他们其实是到不了左右形势改变的程度,他们不是做这种事情的人。
另外一个层面,大学也不行,经典理论也不行,权威大腕儿也是这样。我们看到权威、大腕儿的讲话,自己跟自己打架的太多了。虽然他们不承认,但是我们还是隐隐约约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说过跟现在说的不一样。大学教育能提供什么?它提供的是基础性的知识,要承认这一点,因为提供基础性的知识,结果你就变成权威了,至高无上的一言九鼎的权威了,这是不可能的。你所讲的、所谈的、所做的事情也是基础性的,在尝试范围里面,不可能超越领域、超越这个层面的。我们有一些权威的迷雾,这么一种错误的感觉。就是因为考了一次大学,结果一辈子就要景仰你。很多人真的是这样,但这是错误的迷雾。
很多的事情,我觉得现在都指望不上,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失望,带来了一种失望的情绪,政府、大学、权威、大腕儿都不行。过去讲四极,这第四极就是新闻媒体。所谓四极就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到了媒体就是第四极了。我过去也是真的相信,也很崇拜,当然更多的人比我崇拜的厉害得多了。
我认识了很多人,我的很多朋友过去都是在政府部门、在大学里面工作的,后来新闻媒体开始兴起,内容为王,他们都果断辞职加入到了媒体当中。所以想起来那个年代也很有意思,我们在那个年代看到了很多的报纸,什么《精品购物指南》、《新经济观察》、《二十一世纪》了,最早当然是《中国经济报》了。那些新的新闻媒体是充满活力的,带来了很多新的思想,我当时也很喜欢看,很多人也看,后来有了互联网了,什么网红了,那些投身于这些媒体里的人后来又出来了,当然这是后话。这种成批的进入、舍身投入的这一群体再出来,这也是一个过程。也说明了形势的改变、这种风云的变换。
现在来看,要说媒体是第四极,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是不相信了。我过去是相信的,但是现在我是不信的,因为我看到了媒体里面有太多的毛病——媒体也是可以被收购的,过去我们对华尔街日报是很崇拜的,认为华尔街日报是个很客观的报纸,是经济学家在担保,很多人的水平都非常的高,摆事实讲道理,是建立在数据、指数的基础上去做分析,所以我们很崇拜,认为他很客观。其实早就不是了,华尔街早就不是了。华尔街日报是被默多克收购的,收购了之后他就有了巨大的改变,他的很多报道都是有党派立场的,都是站在某一面来反对另外一面,所以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已经被很多人批判了,如果说你现在还很迷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就说明你已经跟不上世界的改变,跟真实的世界已经产生距离了,你已经不知道世界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改变。
第四极是可以被收购的,是可以被收买的,然后支配它去做某些事情、去达成某种目标。这种情况是有很多的,还有各类指数,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媒体调查。在美国总统的大选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谁的支持率高、谁的支持率低,最后很多预测都是很离谱的预测,关键是做调查的这些机构也是被收购了,背后也有资本的力量,是有支配性的影响力存在。这些支配性的、影响力的存在,就决定了他倾向于什么,他要产出什么样的结果。
我记得拜登总统上台之后,也有一些社会调查,也有数据化、很量化的结果,做的表格、图表都非常漂亮。后来我看到一个美国学者发了个推特,说数据的调查一定是出自白宫之手,它指的是阿富汗问题,对拜登毫无影响。类似的这种荒谬的结果,有很多。
因为这些改变的存在,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最稀缺的就是一种东西——独立性。这种客观性和独立性才是最珍贵的。
我们大家的命运、世界各国的对抗、纷争、贸易战,还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事,那么面对这些大事,我们能靠谁?真正的公众利益我们能够指望这些四极吗?靠大学、权威?还是那些不独立不客观的智库?又或靠那些媒体和新闻媒体、互联网?所有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必须靠真正客观独立的智库,这些客观独立的智库才是未来。
这个世界是真的存在客观独立的智库的。一谈到智库,可能很多人就说,现在的智库好几千家,美国也有好几千家,中国也有好几千家,鬼才知道哪个是独立和不独立的。这个话就长了,但还是有一些清楚的指标和标准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其经济来源。你的经济来源、你的背景,如果证明你是不清不楚的,你是依赖于某一方的,依赖于某一个集团、某一种势力,是被某一种势力所支配和强烈影响的,那就不是独立智库。

真正的独立智库是存在的,像安邦就是一个几十年独立存在的智库,就像我们一直说的,我们就是坚持客观、独立的立场。不是一天、两天,你可以往前查,你可以查到很远的时间,都可以发现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的智库。这种独立的智库是为公众利益而着想的,它是为公众利益而谋划的,它是为了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而服务的,是作为独立智库的一种追求。
所以智库跟智库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独立智库工作,在跟未来紧密相关的独立智库里面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荣幸,这是我的荣幸,我能够有机会去打造这样的一家独立智库,也是我的荣幸,因为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跟未来是紧密相关的,可能也就只有安邦是作为一家独立智库。在西方国家还有很多NGO组织等等,意思差不多,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真正着眼于各自国家的公众利益最大化,以此为追求来展示、研究、追寻、探索,做这些方面的事情。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当然是跟未来紧密相关的。
我觉得在这方面能够谈的事情是非常多的。现在的世界让人们失望的地方越来越多,这种失望的感觉和情绪非常的强烈。我其实在这方面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有这样的很强的失望的情绪。对外界,我也同样感觉很迷茫,因为否定之否定、反对之反对,翻来覆去、颠来倒去的、折腾来、折腾去的,这种事情太多了。
这一方面当然是涉及到个人水平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世界的改变太快,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存在。在这种混乱的、混沌的大世界面前,我们能靠什么,我们肯定不能靠那些人云亦云的机构,不能靠动不动就谈基本常识的机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有前瞻性、能够着眼于未来的研究机构。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种着眼于未来的研究机构身上,这才是唯一的希望。能靠美国总统吗?美国总统四年一届,四年一届之后,新的领导上来,首先把上一任总统任命的这些官员们都开除,然后换上自己的人,过了四年,又换了一批。他是这样换来换去的,一批批的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能靠他们吗?靠不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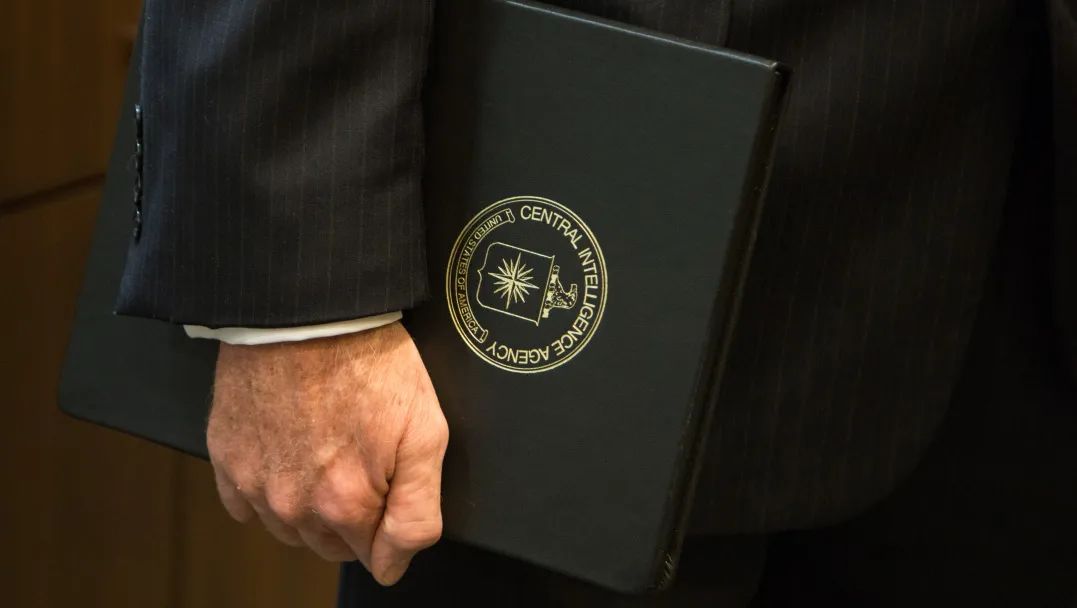
在政策发生急剧转变的风云变化的时期,只能靠独立智库,这是未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荣幸的,我觉得安邦智库能够出现、能够做到今天,我也是很荣幸的,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它绝对不是一种平平常常、淡而无味,提供给你、让你混日子的工作,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的工作。这是一种职责,这是一种涉及到未来的职责,很多时候它还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从我个人的性格来说,一方面是能够肩负这种压力,另外一方面是能够挑战这种压力,如果能够解决问题,那就更幸运了。这当然就跟未来产生了一种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智库平台(安邦智库)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是一种幸福,这是一种能够让我产生价值感的工作。如果做别的,我可能就在风云变幻之中迷失,我可能就会感觉很迷茫。
抬眼望去,云山雾罩,乌云笼罩在头顶,只能抬头、仰望希望找一找乌云密布当中哪个缝隙能够射下一缕阳光,只能这么盼望着。但是现在不是,如果你在安邦工作,你就像气象学家一样,你在探索这些风云变幻,你可以掌握卫星云图,你能够看得见什么时候风云变幻,会出现什么样的改变,什么地方有晴朗的空间、什么地方依然是乌云密布的,你就会知道、掌握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太了不起的工作、太有价值的工作了。
所以我觉得独立智库是未来,能够在独立智库当中工作是一种幸运,对我来说至少是这样。

